回到故事的最初,司马懿虽一身才华见解,却不愿涉足朝堂,后为救父救兄,走上仕途。他可以为了郭照把兵权交给曹真,又为了张春华和司马师把兵权交给曹爽,他变了吗?好像没变。司马懿前半生为大魏竭心尽力,三次受命托孤,多次抵御外敌。面对诸葛亮的激将法,司马懿忍了;面对曹叡的“鸟尽弓藏”,司马懿忍了;面对曹爽骤登高位,几次三番的打压,司马懿也忍了;但面对春华死,曹爽野心不止,司马懿不忍了。他变了吗?好像变了。
司马懿变了,是他沉不住气了吗?柏灵筠说,是他怕了。
司马懿怕了,而这种怕他曾在西城亲口对诸葛亮承认,“我跑过了武帝,我也跑过了文帝,但我总是跑不过,跑不过我自己,心里的恐惧”。那时的他,虽然恐惧,但尚且能忍。此时的司马懿已进入人生的末年,人到老年并不都是看透世事,无忧亦无怖,事实上面对生死和更大的权力,忧惧更深。这种内心的恐惧和外界的威胁,让他与为家而“战”的初衷“背道而驰”。柏灵筠是懂司马懿的,她说“你是因恐惧而杀人,这样卑鄙怯懦的司马懿,我打心里瞧不起你!”是啊,还有什么比真切感受并使用自己手中滔天的权力,更令人安心的呢?但真正的恐惧,是安心过后又卷土重来,是令自己都无法直视自己的恐惧,所以司马懿大声呵斥回去“我做什么不做什么,不是为了让你看得起!”走到这一步,名留青史都随他去,司马懿已无法回头。
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司马懿,《虎啸龙吟》以他为主视角,把司马懿变回一个真正的人,呈现他的好,也不避讳他的坏,正如人性的善恶两面,给予了观众足够的留白。它不渲染不激化,是一场穿梭时空的戏剧与人性的对话。于角色,这是局内人司马懿的自我剖析;于观众,这是评论司马懿时自我意识的外化。这部剧解决了一部分道德困境,润色了人物性格,比如不同于历史上司马懿对张春华的态度,剧中的司马懿和张春华打打闹闹也算相伴了一生,这是在传递创作者的价值观和态度。好的戏剧从来不给观众画一个句号,而是留下一个问号,该剧通过司马懿的一生,提出了关于人心和人性的问题,如果你也有相同的疑问,不妨一起到《虎啸龙吟》中,寻找答案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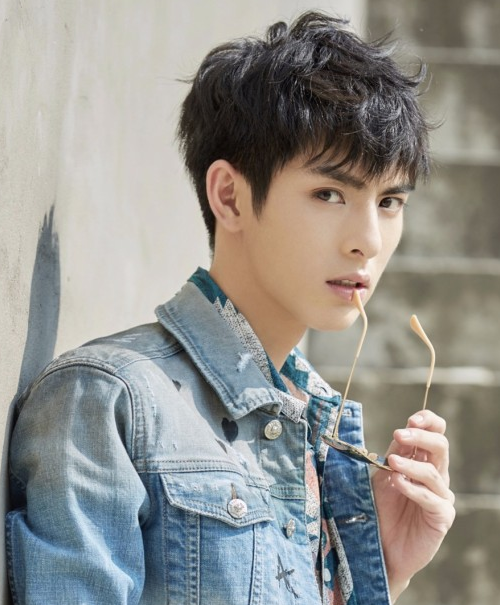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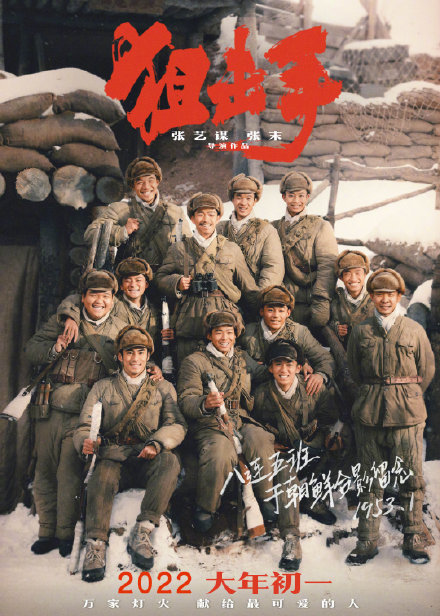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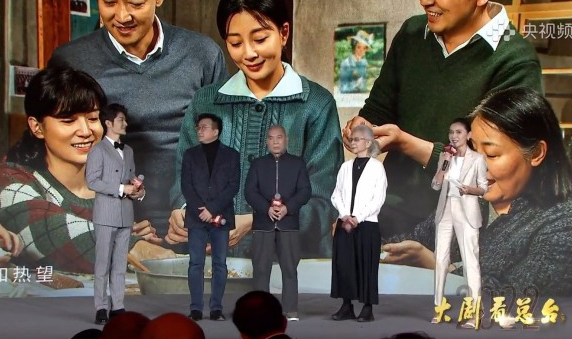






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